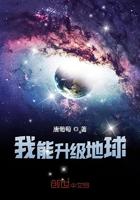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引凤听涛 > 第3章 争(第4页)
第3章 争(第4页)
太阿没有啸吟、也未激出狂风,而是老实的像那儒经里的孝子,安静的被握在他的手中,如一柄寻常铁剑那般。
“师父。”
见小老头剑出鞘,雾中那斗笠客停下脚步,远远的大喝出了声。
“如今弟子的武馆遍布七国,桃李天下,还请师父让了这三才的位置!”
雾中那人说完,也唰的一声剑出了鞘。
“这三才境乃是天定,唯有世上剑道最高之三人能入,我又怎能让得?”
小老头笑谈一句,湖边又静了下来。
三个同行而来的小辈琢磨了一会儿,皆是浑身一凛。三人终是回过味来这三才剑争乃是死斗。老人若是不死,新人便无门可入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叫何一么。”
小老头不去看雾中人,反是端详着太阿。太阿涌起阵阵剑意,吹得这边四人发丝起又落。
“知道。师父是要我的剑道惟精惟一。”
“哎。但为师听说你这逆徒是将这名姓都改了,可有此事?”
“师父,道不同便不相为谋。”
“那今日为师便授你这逆徒最后一剑。从此恩怨两清,莫要再互称师徒了。”
雄浑的剑意自小老头的右臂始,涌上了太阿的剑身,在剑体中徘徊激荡。
呼啸的剑风一圈圈震开了小老头身边的雾,吹的他一身白袍飞扬颠簸、猎猎作响。
须臾间剑意便到了巅峰,太阿轻轻嗡鸣已然承受不住更多的剑意了。小老头轻描淡写的向雾中斗笠客递出一剑。
剑气细不可察、一闪而逝。
何须一见小老头这剑无风无浪,似是失了攻到他那的气力。便将抬起的剑放下,不再防备,脸上有些轻蔑又有些惋惜:
“师父您是老了吧?这剑颇有些虎头蛇尾。”
未等他笑出第二声。
旁侧的那一汪大湖狂涌,湖面有如被这一记剑喝惊醒那般,竟拍出了惊涛骇浪。
层层波涛狂啸着卷过岸边,又磅礴的盖过湖中的土丘,一遍又一遍的打弯了丘顶的树,将整个坡面染的湿黄渗水。
那何须一还站在那,但其身后的庭石假山齐齐的碎成齑粉。齑粉尚未落地,就被狂风鸦飞鹊乱的给卷走了去。
何须一膝盖一软,瘫摔在了地上,脸上僵着先前那轻蔑又惋惜的笑。
一时间人驻足鸟惊飞。
太阿只是轻轻嗡鸣着,一如出剑时那般。
待到鸟散人去,雾也被这一剑冲的淡至几近散去。小老头终是看清了何须一的狼狈模样。
“人活一世,剑存万年。功名利禄不足挂齿,剑客身死后最该余下些的,是这辈子的剑道。”
小老头不知是说与曾经的逆徒听,还是说与眼前的两女听,唏嘘完了这两句便将太阿抛向厌月,双手一背踱着步朝湖边走了。
厌月踉跄的向前跑了两步,稳稳接住了剑,踩着碎步跟了上去。
“走啊,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愣愣的?”,小乞丐皱着眉,一拽甘白尘的衣袖,催着他也跟上。
甘白尘盯着那瘫坐在地上的何须一,先前戴的斗笠已然利落的被劈成两半,一边半个落在草上。
甘白尘又扭头看了看波涛未平的湖面,不由得咽了口唾沫。
这至少隔着五六十丈远的一剑,威力竟能至如此地步。更勿论这剑隔着空仍能有收有放,那斗笠客如今仍好生的喘着气,眼瞧着是没啥大碍。
这高人先前还真没胡吹他的剑术!
“快些着!他俩都走远了!”小乞丐连声催着,将甘白尘从思绪中拉了出来。
小乞丐拉着他赶了几步,追上了先行的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