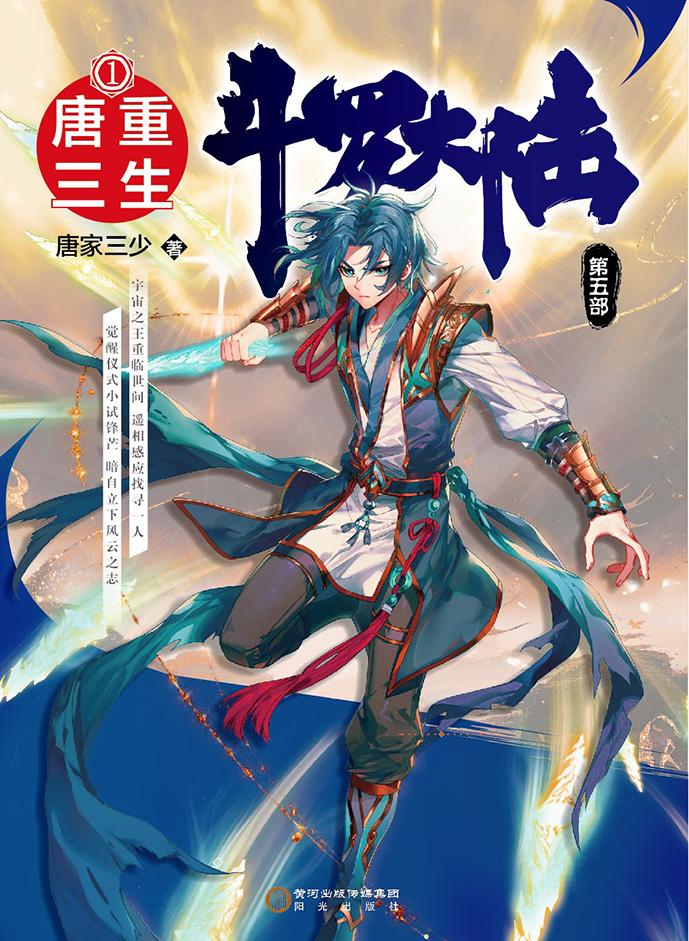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没有主角光环怎么啦 > 第 65 章(第1页)
第 65 章(第1页)
沈殷道:“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沈宅的沈小姐,我小的时候,是在花楼里长大的。”
沈殷的母亲是个歌姬,但是她开始记事的时候,母亲已经不怎么唱歌了。
她是楼里年龄大的歌女,嗓音不比从前空灵,容颜也老去了,虽然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,但有些皱纹总是盖不住。
却还是爱打扮,穿着艳丽衣服在花楼里招摇过市,纤长的手指挟了根长烟杆递到唇边吸一口,然后吐出一口烟圈来。
双唇鲜红,指甲上染的蔻丹也是鲜红色的,端的是一个光鲜亮丽。
沈殷却完全与之相反。
她得在花楼里干活,脏活累活什么活都干,一天到晚都是蓬头垢面的,甚至可以说是邋里邋遢。有时候深冬,还要替她娘洗衣服,一双手泡在冰水里,冻得通红。
有人路过,瞧见她生满冻疮的一双手,叹一句:“可怜哦。”
她娘长眉一拧:“可怜什么?她长了张嘴要吃饭,我辛辛苦苦卖唱赚钱,她不干活,难道给她白吃饭?”
沈殷抿了抿唇,也不说话,默默地用力搓着衣服。
花楼里长起来的小孩是没有爹的,又过了几年,沈殷连娘也没有了。
她娘病死在自己的房间里,死的时候,形销骨立,松垮垮一件华服套在身上,锁骨凸出得吓人。
沈殷无处可去。
她一个没什么见识的小姑娘,什么也不会,就还是留在花楼里当丫鬟,动辄被人打骂。
有时还听旁人议论她母亲,说她年轻的时候极美,偏偏脑子不清醒,要生下这么个拖油瓶,从此性格变得奇差,人气也随之一落千丈。若非如此,凭她年轻时候的姿色,轻易就能被人买回家去,住在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,什么也不消做,只做一只精致的金丝雀。
沈殷干着活,懵懵懂懂地想,她母亲喜爱穿艳丽的衣衫,有时也穿大金色,发间缀着些翎羽做装饰,确实很像美丽的鸟雀。
但沈殷没想到,她母亲没做成的金丝雀,她倒做成了。
变故发生在她十二岁的那年,有人给她置办了大宅子,说要收她做义女。
那个男人隔着屏风见她,说话的语气也是小心翼翼的,他说:“我有一个早夭的女儿,同你长得特别像。我……可以供你吃供你住,你就住在这里,好么?就像她还在一样。”
沈殷觉得莫名其妙。
可是她在花楼时,虽然是个打杂的,也是同人家签了卖身契的。那么既然现在这个有钱老爷买下了她,当然是老爷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
就稀里糊涂的在大宅子里住下了。
她名叫沈殷,那大宅子大门上挂了牌匾,就叫沈宅。
住下以后,老爷却是不常来,只是经常托人来看看,看她府上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有,有没有哪里缺了什么,有没有什么不方便。
有时得了些稀奇的玩具或珍宝,也差人送过来。
沈殷从小清贫惯了,对那些东西并不十分感兴趣,只是有时候瞧见好看的,忍不住多看两眼,就叫人拿去冬暖阁存放着。
平日里大多数时候,沈殷总是在想,这个老爷,真的很有问题——
他说是想女儿,可是把她养起来之后,看也不来看,好像只想养着她似的。
再说了,义女,为什么要用另外一座宅子藏起来,大大方方地直接接进府里不好吗?
沈殷自小生在花楼,也算见识广博。
她思虑良久,某一天脑子里突然闪过花楼里的歌女所说的“金丝雀”,突然顿悟了——
这位老爷,大约是想收她做二房,无奈家有悍妻,所以只好将她养在外头,藏起来。
什么义女,不过是个幌子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