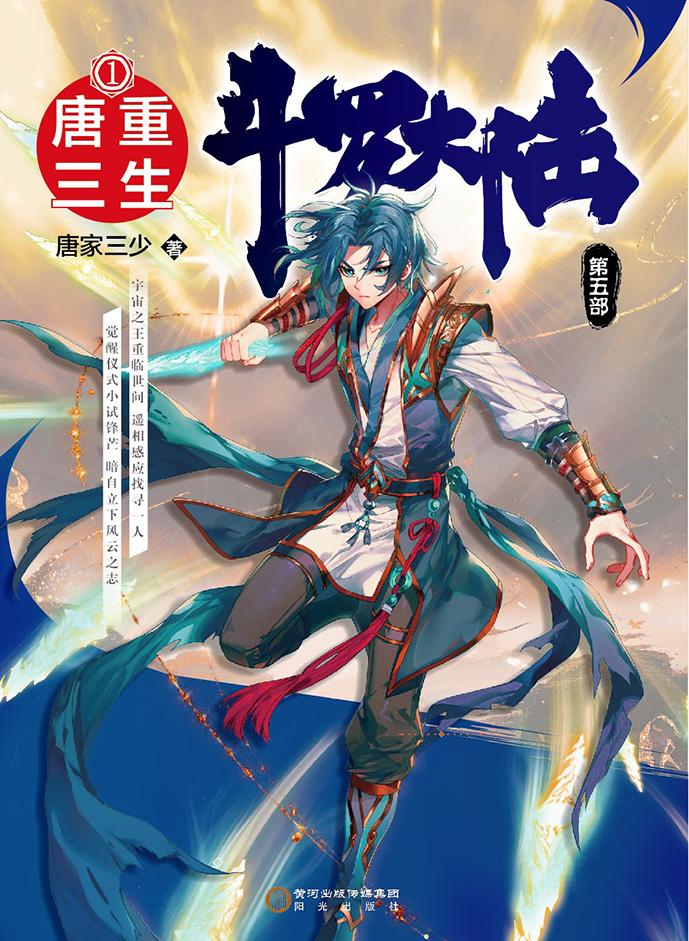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没有主角光环怎么啦 > 第 65 章(第2页)
第 65 章(第2页)
想通了这一点,沈殷咬牙切齿地捏紧拳头:“这个禽兽!我才十二岁!”
但是她也没什么办法,她是封建环境里长大的女孩子,被人买走了做二房,难道还能反抗吗?就吃住都在这里。
沈殷又想起自己在花楼打杂时的所见所闻,觉得自古有多少家庭,就是被这种养在外头的外室给破坏的。
现如今,她成了破坏人家家庭的人了,就算是迫不得已,到底是一种罪过。
于是她开始每月初一上佛堂念经,每月十五去乞儿街施粥。
四下无人的时候,沈殷跪在佛像前的蒲团上,双手合十,虔诚地为自己赎罪:“佛祖呀,我不是诚心做坏人。行这些微不足道的善事,就当为自己积点阴德,也想消一消今生的业障,您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要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,好么?”
沈殷说到这里时,整个人已经放松了许多。
她用两手托着下巴,手肘抵在井沿上,幽幽地叹了一口气:“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那有钱老爷就是我们临川城的城主,听说他是个顶顶好的人。养外室这种事,毕竟于名声有损,难怪要将我藏起来。”
她后来想,佛祖应该是没有听到她的祈愿的。
又可能,佛祖其实听到了。
可是看看她这个人,被人藏在沈宅里,吃穿用度,都是旁人供着;施粥行善,也是慷他人之慨;唯有求佛时有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诚心,可所求所想,都是自己。
她的善良都是假善良,是充满私心的。
因此佛祖并不应承她。
所以那一天,她出城求医,过北城桥的时候,佛祖要让她的马车撞上个小女孩,连人带车一起跌进河里去。
她始终是有罪的。
这罪孽还在不断的加深,甚至从桥上跌下去的时候,还要拖累一个无辜小女孩。
叶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,她呆愣半晌,愣愣道:“那个小女孩——”
那个小女孩可真不无辜。
但叶岑将话起了个头,却不知该怎么说下去。她觉得沈殷才是真真切切一朵小白莲,托着病体从桥上那样跌下去,想的却是自己害死了旁人。
她想了想,道:“你也不该那样想。钱是范城主的钱,若非有你,那些钱就被用到了别处,也不会成了穷苦人家的口中食了。再说了,谁会来管你做好事的动机是什么呢?你帮助了人,这是实实在在的呀。君子论迹不论心嘛。”
“君子?可是、可……”沈殷瞪大了眼,惊诧的看着叶岑,不知何时垂落到身侧的手局促地搓了搓衣角,“可我只是个小女子呀。”
叶岑想也不想:“那又怎么了?那些好事,就是你一个小女子做的呀。”
话是这样说,叶岑却总觉得,还是有哪里不太对劲。
但沈殷的逻辑是如此自洽,她突然地张了张嘴,又不知该从何问起。
于是便沉默下来。
良久,沈殷却忽然开口问道:“从桥上跌下去的时候,我其实就已经摔死了,对么?”
叶岑一愣。
沈殷道:“我坠河我失去意识之后,好像做了很长的一场梦,梦中偶尔有人来看我,还会给我喂些什么东西‘吃’。兴许是范老爷救了我,他是个神通广大的城主,总有些法子能救我,但是他喂给我吃的那些东西……”
她顿了顿,脸色有些发白,眼眶又红了一圈,但这回忍着没有哭:“他救活我,害了许多无辜人吗?”
她不是个见识很多的人,但那毕竟是她自己的身体,在没人比她更能清晰地感受她自己的生命。
梦境的最开始,她是破碎的、枯槁的、全然没有生息的,可随着那人一次一次来看她,她觉得自己像一株重新汲取到水分的枯草,不能自已地一点一点将那养料吸纳进身体里,于是她重新活过来,有了新的生命力。
沈殷自问不是个高尚的人,可她像许多普通人一样,有着最朴素的善恶观。
她知道她“吃”下去的是什么东西,也知道那样是不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