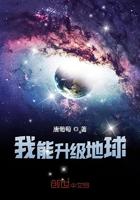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我真没想霍霍娱乐圈 > 576章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存货100首(第3页)
576章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存货100首(第3页)
“煮点槐花水。”他说,声音在寂静厨房里显得格外清晰,“洛兰说她喜欢清苦后回甘的味道。这花,苦在初尝,甜在舌根。跟那首歌一样。”
水沸,白雾升腾,裹挟着清冽微涩的香气,弥漫整个公寓。
孙承宇倚在厨房门口,看着苏小武侧影。暖光勾勒他下颌线,睫毛在蒸汽里轻轻颤动,像蝴蝶振翅。他忽然开口:“大武,你有没有想过……为什么非得是《ScarboroughFair》?”
苏小武搅动砂锅的手顿了顿。
“因为……”他望着水面上浮沉的槐花瓣,声音轻得像叹息,“这首歌里,有四个意象——欧芹、鼠尾草、迷迭香、百里香。古时候人们用它们驱邪、安魂、纪念逝者。可洛兰唱的时候,我把‘rosemary’换成了‘hawthorn’——山楂。咱们这边的山楂,开白花,结果酸,入药治心悸。”
他舀起一勺水,凑近鼻尖闻了闻:“你闻,是不是有点像……小时候发烧,奶奶熬的那碗山楂水?”
孙承宇没说话,只是默默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打开备忘录,新建一页,输入标题:
《ScarboroughFair(HawthornEdition)》
作曲:南北
演唱:洛兰·布莱曼
特别致谢:京都槐树,山楂花,以及所有把苦味熬成甜味的人。
窗外,东方天际已透出极淡的青灰。
凌晨四点整,熊猫动态后台弹出一条系统通知:
【您的动态《深夜偶得,与布莱曼女士即兴合作》已被全球超过217个国家及地区用户标记为“值得反复聆听”。】
苏小武关掉灶火,将第一碗槐花水端到客厅,放在罗辉飞面前。
热气袅袅,蒸腾而上,模糊了电视屏幕里循环播放的奥运闭幕式画面——焰火如金雨倾泻,照亮无数张仰起的、含泪微笑的脸。
他坐下,没碰水,只静静望着窗外。
天快亮了。
可有些东西,早在昨夜就已悄然破土。
比如那首歌。
比如那个名字。
比如当洛兰·布莱曼把斯卡布罗集市搬来京都,而苏小武把槐花山楂种进英伦民谣的土壤时,世界忽然发现:所谓文化壁垒,原来不过是两扇没推开的门。而开门的人,有时只是凌晨三点,煮一碗槐花水的普通人。
罗辉飞捧起碗,喝了一口。
微苦。
继而回甘。
他抬头,看见苏小武正用手机拍摄窗外渐明的天色,镜头缓缓下移,掠过楼下早点摊刚支起的蒸笼,白雾滚滚,热气冲天;掠过晨跑青年耳机线里漏出的、不成调的《ScarboroughFair》哼唱;最后,停在公寓楼对面那面老旧砖墙上——不知谁夜里用喷漆涂了一行歪歪扭扭的英文,颜料未干,墨迹淋漓:
**“THEFAIRISHERE。”**
苏小武按下拍摄键。
视频十秒。
无声。
只有天光一寸寸漫过砖墙,浸染那行字,像温柔潮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