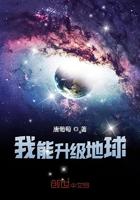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我真没想霍霍娱乐圈 > 576章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存货100首(第2页)
576章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存货100首(第2页)
他圈出星轨录音棚,标上红点;圈出洛兰下榻的四季酒店,标上蓝点;再用虚线连起两点之间所有可能的路线——地铁、出租车、共享单车停放点、甚至步行捷径的梧桐树荫覆盖率。最后,他在两条线交汇处,重重打了个叉:**“明天上午十点,四季酒店B座一层咖啡厅。”**
“他们约的?”孙承宇问。
“她约的。”苏小武合上本子,“半小时前发的消息。说‘想再听一次钢琴声,不带观众,不带麦克风,就我们俩’。”
“就……就你们俩?”罗辉飞猛地坐直,“她经纪人呢?翻译呢?随行律师呢?”
“没提。”苏小武耸肩,“就写了句‘bringyourkeys’。”
“钥匙?什么钥匙?”
“钢琴钥匙。”苏小武指指自己心口,“还有,她房间门卡——她发了张照片,是房卡背面,手写编号,下面画了个笑脸。”
孙承宇和苏小武对视一眼,同时笑了。
罗辉飞却突然安静下来。
他盯着苏小武桌上那台笔记本电脑,屏幕还停留在熊猫动态页面。视频下方,最新一条粉丝留言刚刚刷新,ID是“老槐树下听雨”,头像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:七十年代京都胡同口,一棵虬枝盘结的老槐树,树影斑驳,树下石阶上坐着个穿蓝布衫的小男孩,抱着把断了两根弦的旧琵琶。
留言只有七个字:
*“这调子……像我爷拉的。”*
罗辉飞手指悬在屏幕上方,迟迟没点下去。
他忽然想起十年前,自己还是星轨一个跑外联的小编导,第一次见苏小武——那时他刚退伍,在部队文工团待了八年,复员后揣着本破旧手抄谱,背着把二手吉他,闯进星轨面试间。没人信他能写歌,直到他即兴弹唱了一段《槐花几时开》,调子是川南小调,和声却用了肖邦夜曲的织体,副歌一句“槐花落进搪瓷缸”,唱得满屋人眼眶发热。
当时负责终审的,正是常仲谦。
常仲谦听完,没说话,只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磁带,塞进老式录音机,按了播放键。
里面是1957年中央广播乐团录制的《二泉映月》现场版,阿炳亲传弟子演奏,弓弦震颤如泣如诉。
“听见没?”常仲谦指着喇叭,“人家拉琴,拉的是命。你唱歌,能不能也唱出命来?”
苏小武当时低头想了五分钟,然后说:“老师,我想试试把二胡的滑音,变成钢琴里的踏板延音。”
现在,十年过去。
他真的把二胡的命,活成了钢琴的魂;把斯卡布罗的海风,吹进了京都的槐花巷。
罗辉飞喉结滚动了一下,终于点开那条评论,郑重其事地回复:
*“您爷拉的,一定很准。”*
发送。
他放下手机,长长呼出一口气,仿佛卸下了十年积压的某种执念。
“饿了。”苏小武忽然说。
“啊?”
“饿了。”他站起来,趿拉着拖鞋往厨房走,“凌晨三点,得吃点东西。不然待会儿见洛兰,饿得手抖,弹错音,她该以为我在敷衍她了。”
冰箱门拉开,冷光倾泻。
里面整齐码着三样东西:一盒未开封的速食螺蛳粉,一罐云南玫瑰酱,还有一小袋晒干的槐花——是他上周回老家,亲手从老屋院里那棵百年槐树上摘的,用牛皮纸包着,搁在冰箱最上层,像供着一件圣物。
苏小武取出槐花,又翻出个小砂锅,接水,点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