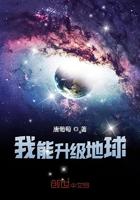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情迷1942(二战德国) > 风车(第3页)
风车(第3页)
他已经低头,利落拨开她睡裙领口,锁骨往下,有一串更显眼的红痕,是他留下的,在白皙皮肤上格外触目惊心,如同雪地里落了一树的红梅。
“扯平了。”他像验收战利品般端详,语气里带着恶劣的满足,指腹按上最红的那处,激得她浑身一颤。
俞琬慌忙把领口攥紧拉好,连耳朵尖都红得透明。
男人低笑,终于松开她,坐起身,白衬衫在晨光中透出肩背结实的肌肉线条,一头金发睡得凌乱,难得显出几分慵懒。
“起床。”说着,他单手把她捞起来,“今天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“去哪儿?”她懵懵懂懂。
“秘密。”克莱恩难得卖关子,眼里掠过一丝孩子气的狡黠,他下床,取下村长女人准备的红色毛呢外套扔到她怀里,“穿厚点,外面有风。”
他们走出村长家时,整个布勒克村刚刚苏醒。
麦茬地里凝结着薄薄的霜,几只奶牛在草地上吃草,脖子上挂的铃铛叮当作响。
井边有妇女在打水,看见他们,动作明显顿了顿,便又低下头继续做事,但那几道目光的余温,依然黏在他们交握的手上。
一个德国上校牵着一个东方女人,在荷兰村庄的清晨散步。这画面荒诞得如同被强行插入纪实影片的浪漫桥段。
克莱恩当然感觉到了那些目光。刚出门,那只小手就凉得厉害,他知道她在想什么,那破农舍不隔音,昨天的动静怕是连村口的牧羊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此刻她脸都快红透了,低着头看着鞋尖,恨不得把自己缩进他影子里。
做都做了,咬也咬了,脸皮还薄得要命,他轻嗤一声,手上却握得更紧了些。
“看,面包房。”她突然轻声说,指尖轻轻戳了戳他掌心。
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。胖面包师正在摆弄刚出炉的黑麦面包,焦香飘得满街都是。
男人停下脚步,掏出几张荷兰盾走过去,“两个面包。”
面包师眉毛快扬到额角去,显是没想到这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德国男人还会主动给钱,愣了一下才僵硬地接过,立刻包了两个最大的递过来。“给您和…。夫人的”
夫人。
克莱恩嘴角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,甫一接过便往回走。可没走两步便弯下腰,长臂一揽,便将女孩打横抱起来。
“呀!”她小声惊呼,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。
“不是怕被人看?”他看她,脚步没停,“把脸埋好。”
她倒还真言听计从,把脸颊贴到他颈窝,整个人都缩进他怀里去,只留半截耳尖露在外面。
这姿势就对了,他抱着她往前走,感觉怀里那点不安分的挣动渐渐平息下来。
路过一个爬满蓝色牵牛花的小院时,一个小姑娘正扒着篱笆探头探脑,看见他们,眼睛瞪得圆溜溜的。
“文医生!”女孩朝俞琬欢快挥手,又怯生生看了眼那个金头发上校,声音弱了下去。“……你的腿受伤了吗?”
俞琬瞬间就说不出通顺的话来了,“没、不是…。”她挣扎着就要下来,却只被箍得更牢靠些,半分都动不了。
头顶传来男人四平八稳声音:“嗯,伤了。”
“严重吗?”小女孩踮起脚尖,眼睛里满是担心。
“很严重,所以要好好照顾。”
安妮用力点头,小辫子跟着一晃一晃:“那你…。一定要抱稳哦,文医生千万不要乱动,乱动的话……”她皱起鼻子,努力回忆着自己上次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时母亲的话,“……骨头会长歪的!”
“会的。”他一本正经应着,随即低下头。“听见没,别乱动。”
啧,小孩真麻烦。
可当目光落在怀中人鸵鸟般埋着的侧脸时,他又觉得,偶尔听听童言童语倒也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