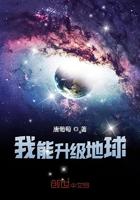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情迷1942(二战德国) > 风车(第2页)
风车(第2页)
她怔怔望着他,连嘴里的酸味都忘了。
他很少这样笑,在巴黎时偶尔有过,但更多的是那种军人式的,带着叁分痞气的笑。这是个全然放松的笑。
在这个战争与战争之间的缝隙里。
“傻了?”他伸手,拇指擦掉她唇角的果酱,堂而皇之地含进自己嘴里。“像只偷吃的小猫。”
她这才回过神来,羞恼地抬手掐他手臂,这回攒足了力气,可对男人来说却更像是在撒娇。
他们分食着同一碗炖菜,同一块涂满草莓果酱的面包,同一杯苹果酒。她酒量小,才喝了两小口脸就红了,眼睛水汪汪的。
克莱恩看着,又不自觉心猿意马起来。
此时,落日余晖正透过格栅窗撒进来,远处风车慢悠悠转动,一群白嘴鸦掠过天空。汉森太太哼唱的民谣飘进餐厅,古老的调子里藏着战前岁月的安宁。
这一刻她竟恍惚觉得,那些炮火,逃亡,都成了上辈子的事,仿佛他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,在某个傍晚,分享着最平常的一餐。
这顿晚餐,大家谁也没多说话,就这么静静地吃着,吃得极认真,像是生怕它早点结束似的。
克莱恩收紧手臂,让她更深地陷在自己怀里,呼吸着她发间淡淡的玫瑰香,这是几个月来,第一个他真正放松下神经的时刻。
因为她在,因为她现在好好在他怀里。
窗外,最后一丝霞光沉入地平线,汉森太太的哼唱停了,厨房传来洗碗的水声。
“晚上想做什么?”
她仰起脸,许是今天累着了,又被允许多喝了几口酒,眼睛雾蒙蒙的:“……不知道。”
“还疼吗?”他问,手指在她腰侧不轻不重地揉。
“嗯…。。好点了……”女孩正是饭饱神虚的时候,又被上校牌专属按摩伺候地舒服极了,整个人软得像只被顺毛的猫,思绪飘忽间,她往他怀里蹭了蹭,哼唧了一声。
而在她懒洋洋抬眼,撞进男人那双翻滚着欲念的眼眸时,所有睡意又立时烟消云散了。
“那晚上就再做。”
第二天清晨,俞琬是在一个过分温暖的怀抱里醒来的。
不是她自己滚过去的,她睡相一直很好,像只缩成一团的兔子,是克莱恩,不知什么时候把她整个捞进了怀里去的。
她睁开眼,视线所及是他凸起的喉结,还有下方一小片皮肤上鲜明的红痕。晨光从窗帘缝漏进来,将齿印照得愈发清晰起来。
那是她昨晚被逼急了时,迷迷糊糊咬下的。
俞琬的脸腾地烧起来,想悄悄从他怀里挪出来,可只动了动,腰间铁臂便立刻收紧了。
“你…。醒了?”她小声道。
“被你盯醒的。”克莱恩终于睁开眼。
其实他早就醒了,只是看了她很久,看她睫毛在梦中轻颤,看她无意识咬着的唇瓣上还带着昨夜被吮破的伤口,久到云雀开始啼叫,久到。。。。。。他必须承认,自己舍不得起身。
他的视线顺着她目光落在自己脖颈处,眉梢微挑:“哦,这个。”
此时的俞琬,恨不得把自己埋进枕头里,却被他轻轻抬起下巴,逼她看向自己。
“兔子急了也咬人。”他拇指重重碾过她下唇,“昨晚是谁先动口的?”
“是你先……”她的辩解弱了下去。
是,是他先吻她,在教堂彩窗投下的光影里,在壁炉火星迸溅的暖光前。可后来。。。。。。后来是她揪着他的衬衫领口,像宣示主权般在那处留下印记,幼稚得不像话。
“我看看。”克莱恩忽然说。
“看什么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