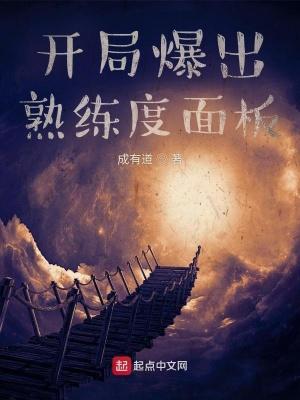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住在你的星球上[青梅竹马] > 第019号星球(第3页)
第019号星球(第3页)
不在同属校区,同一屋檐下,谢星鄞没那么清楚。但他知道,她一定是忙于约会,连网球爱好都疏于维持。
人本就懒惰,自律完全泯灭人性。所以当一个人认真而一以贯之地做一件事,甚至是多件事,身上自会闪闪发光到让人挪不开眼。
谢星鄞承认,即使他不喜欢陆满月,也一定会被她吸引。
可她现在黯淡得和旁人无异,和路边一块石头没有区别,庸俗得如同宿舍楼下的任何情侣。
谢星鄞不止一次地这么在心里对自己说,但掌心的沙,落了满地,回过神时,已经半截入了自己埋设的沙堆围城。
他得空找了个时间去她学校。远远地伫立在操场旁,眺向正在长跑的她。
燕北的一月已经冷到零下五度,寻常人出门至少里三层外三层,何况一个从未北上的南方人。
也许跑过的一圈已经令她血液高速流动,陆满月慢跑时,只穿单薄的冲锋衣和瑜伽裤。
继十一月下过的那场雪之后,燕北只降温不降雪,但在陆满月即将跑向他面前时,空中离奇地落了细碎的雪。
谢星鄞没有在意落在身上的雪,目光直挺挺地投向她,眼也不眨一下。他以为他足够隐蔽,或者她足够专注,竟不曾想她也会看到他,且还慢慢放缓了步伐。
近一个月不见,他远比他想象中要想她。
陆满月只是看了眼他,流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、称不上厌恶的情绪,然后加快步子继续顺着跑道跑。
没什么罗曼蒂克,也没什么风花雪月。只是她跑过来时,对上视线,下了一场雪,而他的心脏也和以往一般跳动着。
回到出租屋,谢星鄞打开的某个文档,循环播放数十次,又不复冷静,难以自持地正视这段备受折磨的感情。
他擅自将今天的雪当做是陆满月送的,所以一月一日的元旦,他想把过去制成的粒子特效以烟花的形式放给她看。
他清楚,陆满月不再会邀请他参与她的任何一场生日。所以想融入进去,只能借用她不知情,又绝对会看见的方式。
从选择合规又大众的燃放场景,再到寻找公司合作编排设计,备案宣发,风险预测,谢星鄞忙前忙后几乎花了一整月。
他不确定陆满月会不会真的到场,所以现场至少还安排了多个机位事实直播录播。
她总该要上网的,总该会看到视频,或者从朋友室友那里听说,嗳你知道吗?江湾广场放了一场超大型的烟花,特别好看,你怎么没去呀?然后秉持着好奇心点开一小段推送来的剪辑。
燕北因为政策,逢年过节也基本禁止燃放烟花,所以这个项目是他目前为止做过的最烧钱。
但,他也不为了庆贺新年。不过是恰巧在这个时候,恰巧在所有人倒计时跨年时,为一个他喜欢的但不喜欢他的女孩放一场,以她为名的生日烟火。
烟花秀开展得顺利,人也确实走到江边特等席在看。
谢星鄞眯眼,在停泊的游轮里认真地回望人群里正中心的她。
而她身边站着另一个男人。与她形影相近,寸步不离,亲密得如同五岁时的他和她。
收到她的新年贺词时,谢星鄞想过置之不理,可是指针停在十二整点时,他又难以自持,鬼使神差地发去祝福词。
“生日快乐,还有,元旦快乐,满月。”
他压低了嗓音,用一如往常的温和腔调,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