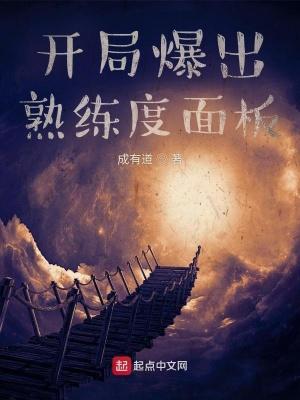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住在你的星球上[青梅竹马] > 第019号星球(第1页)
第019号星球(第1页)
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独处。
陆满月坐得拘谨,言行举止都无不透露着不安和紧促。
谢星鄞很少见她这副样子,印象里,她总是人群中最安稳自洽的人。大概是因为喜欢一个人,所以才不由自主变成另一副模样。
他并非不忌恨柯裕阳拥有这份殊荣,但比起让她不安无措,他反倒宽慰于自己可以让她和往常一般放松。
他们的谈话有一搭没一搭,乏味到让人听得厌倦。谢星鄞拧着门,却仍一瞬不错地凝瞩,直到他们结束闲谈,一前一后地走出房门。
被她完全不留情面的推开拒绝,见她以截然相反的态度迎合他人,他理应就此放弃。但怪异的是,他心里仍然存有一丝希冀。
谢星鄞无比确信,陆满月是一时被新鲜感冲昏头脑,也无比清楚柯裕阳并不适合她。但这道信念并不能消解那丝不平衡。
他冷冷轻哂,想过要去惩罚这个有眼不识珠的女孩,但他不论如何构想,也始终会在心里否决那些一个又一个的惩戒提案。
熟悉她的喜恶,想施以同等的痛苦让她遭受报应,分明是易如反掌的事。可他心里便是百般不情愿,被设想中的她落下的眼泪所刺痛。
十二岁以后,陆满月几乎很少落泪,眼泪全然是个稀罕物,脸扭伤擦伤骨折都难以让她动容,所以他到底为何刺痛?这分明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
如果不被她喜欢,被她厌恶到烦心落泪,不也同样有着同等的情绪价值。
只是想让她难以忘怀,直至十几二十年后也能想他想得皱眉捶胸顿足,那么,这有为什么不可以?
他大概是贪心的。
尤其在看见她喜欢上别人的时候。
如果陆满月从不为情所动,从不喜欢任何人,他可以接受她讨厌他。
但如果她确实有喜欢他人的能力,而他并不能被她喜欢,他感到不平衡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他们走后,谢星鄞也离开公寓。驱车行驶在大道上,越入无人郊区,他踩着油门让车速越来越快,在几近要冲破阈值时,又稳稳停驶海岸边的护栏,在血液喷张里感受动荡的心腔。
谢星鄞仰头,双手扶着方向盘,缓过两回呼吸,拧开扶手箱里的小瓶一饮大半。
他庆幸自己脑子还清醒,没有真的冲昏头脑舍命开进海里。证明他也没有那么喜欢陆满月。
谢星鄞凉薄地扯动唇角,轻哂一息。
之后他回去那间狭小的出租屋,没再去过公寓,也长久的,没有去想她,见她。
其实他不需要主动切断联系。因为陆满月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不依赖他,甚至是故意避嫌。一旦他真的停下来,不念不想不听不闻,那么有关陆满月的所有风吹草动,只会是他凭空的臆想。
关注陆满月,是谢星鄞活了十八年来唯一乐此不疲的癖好。
一味地压抑就像掌心里握住的沙,越压抑,握得越紧,沙子从指缝间就流淌得更快。
在见不到她的第二十三天时,谢星鄞又梦见她,做了一场艳糜的梦。
他如往常般洗冷水澡,拆下四件套塞入洗衣机,换上崭新纯白的备用套。深吸气,没有多逗留,提着公文包里的电脑去学校。
可有可无的课程竞赛,枯燥的编程代码充斥着他的生活,不至于忙到透不过气,所以每天至少花两个钟头跑步散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