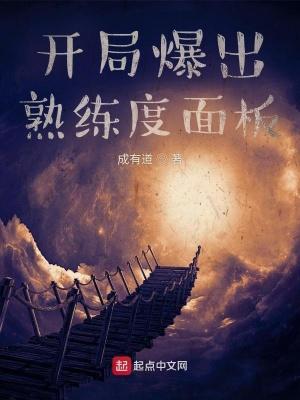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住在你的星球上[青梅竹马] > 第018号星球(第2页)
第018号星球(第2页)
-
衬衣被洗净送回的那天,谢星鄞没有回去,只加价让骑手再跑一趟送到学校。
比之公寓,宿舍的确拥挤。但对他来说,只要有一台可操作的电脑,几件换洗衣物,一张足够让他整个人躺下休息的床,就足够满足生存条件。
‘由奢入俭难’这句话在他身上不起效。寄住在陆满月家的十余年,已经让他习惯逼仄的、隔音没那么好的环境。
但相比起听到室友打游戏的嘈杂噪音,他还是更喜欢独处。
夜里十点,图书馆关门,他不得不回宿舍。如果需要安静的环境,他也不是不能在外开一间房住酒店。
谢家提供的资金不是笔小数目,抛去这部分,他从生父那里继承的遗产也是他八辈子都花不完的,可他就是攒着,分毫不动地放在账户里。
他并非圣人,不屑这笔‘飞来横财’,否则当初又怎会认祖归宗?他潜意识留有囤积的观念。在得知谢家需要他继承遗产时,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,而是遗憾和不忿。
遗憾乍富得太晚,晚到陆满月已经放弃走那条喜欢的路,不忿他们的虚假,连一个同样备考的高三生都不肯接洽。
十二岁时,陆满月向往打网球,用天赋和耐力身体力行地证明自己足够拥有培养资格,却被高昂的训练费拒之门外。
到头来,他只能用积攒大半年的零花钱,给她买了一把质量还算上乘的网球拍。
陆满月笑了,却也哭了。她抹把泪,指责他乱花钱:“我现在走田径,又不打这个,你买给我干什么?一千块嗳!都够买一台手机了!而且只有网球拍没有网球算什么,练手臂吗?”
“都怪你,这个假期我也要帮忙家里干活,都不能出去玩了,不然怎么把钱给你啊?你说你是不是故意让我欠你钱……”
一千块。
放在今天不过是他账户余额最不起眼的零头,陆满月却整整攒了大半年,直到年底领了红包才还给他。
谢星鄞没有收。他自然是故意而为之。
他想看看陆满月这个好胜心比天高的人,一旦欠钱了会有多生气。
他也做到了。他看到她眼睛瞪得溜圆,厚唇抿成一条线,板正地拿出一张红包,对他说:“嗳,还给你。”
“我不要。”他拒绝。
“你不要?”她音量骤然拔高,“那你要干嘛,嫌钱少吗?”
谢星鄞淡道:“我要你拿网球拍陪我打。”
陆满月顿了下,嫌弃:“不要,你菜。”
“我练过了。”他微微一笑,“还是你怕了?”
她的胜负欲太好被挑起,一点即燃。
谢星鄞如愿和她打了一个来回,然后惨败。
他确实技不如人。何况拿着一把两元店网球拍就上阵的陆满月,如果没有任何天赋,怎会被教练相中。
“都说了你菜,你还不信。这下好了吧,脚都崴了。”陆满月居高临下地睥睨他,热汗淋漓,渗透了她的发间和衣领。
她嘴上不饶人,却还是蹲身下来,替他查看淤青,擦拭伤口。
十三岁,陆满月发育得明显,胸前已经有了圆缓的起伏。他别开面不看,反被她钳住手腕,凑上来问:“手腕疼不疼?”
她便是这般亲近得自如。虽不再肆意亲吻他的面颊,但总能浸染他的鼻息,令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心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