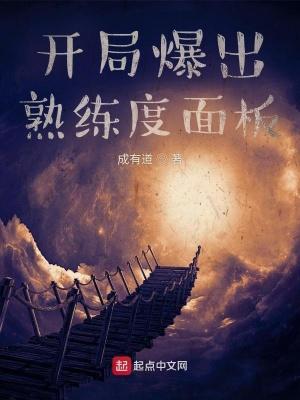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[全职猎人]燃烧火红眼的肖像 > 求助x失落的你x诚实心(第2页)
求助x失落的你x诚实心(第2页)
他这么说的时候,维瑟拉特都已经准备回去了,迈出的步伐咚一下钉在木地板上,她的动作也随之停了几秒,而后才突兀地拧过身子,看向酷拉皮卡,嘴唇几乎没动,从齿缝里挤出拒绝。
“不行。”
说着这话的她带着一如既往的平淡面孔,话语里也听不出什么鲜明的兴趣,可总觉得除此之外她的每部分都透着抗拒,包括一下子就垂下去的风衣。
酷拉皮卡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拒绝,在他看来,这是比佯装无事发生更好一点的处理方法。
“亚里砂会谅解你的。你们是朋友,不是吗?”
“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没有理由。我觉得不行。”
酷拉皮卡合拢文件夹,很认真地看着她,“你在担心什么事吗?可以告诉我的。”
这次得到的回应终于不是“不行”了。事实上,维瑟拉特根本就没有给出回应,只有嘴角极小幅度地往下方撇下去,目光也一并收走,不再继续看他,打算直接回去,却忽然被攥住了手腕,比锁链的崎岖更先一步到达的是一点点温暖。
和梦里很相似,酷拉皮卡的掌心里藏着暖意。
是了,现在居然多多少少能感觉到一点温度了,真奇怪——会觉得丢失的东西重新被找回这事奇怪的她才是真正奇怪的吧?可惜维瑟拉特是肯定意识不到这点的。
不管怎么说,既然有人阻拦了自己,那她就得停下脚步才行。酷拉皮卡把自己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,问她是否在担心什么事。现在维瑟拉特终于开始思考他的问题了,刚才完全是不情愿去想,计划着溜之大吉而已。
但实际上,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思考,理由很简单,她会直白地说出来:“我没有在担心任何事。”
依然是不太诚实的回答,逃避的意味太重了。
酷拉皮卡绕到她的前方,很认真地看着她。这样就无处可逃了,他这么想着,接着说:“按照你的说法,不就没有不和亚里砂坦白丢失记忆的理由了嘛。”
“是的。”确实是这个道理没错。
“那就告诉她吧?”
“不行。”
“可你明明没办法给你拒绝的理由。我肯定不是非要逼迫你做什么事,只是觉得,无论如何亚里砂肯定都能体谅你,向她敞开心扉说出一切是完全没关系的。”
或许在担心的人是他——酷拉皮卡不希望自己才是她说出“不行”的原因,也不希望自己是她拒绝共享一切的角色。哪怕她甚至连某人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了他,他还是不受控制地担心与她有关的事情会从指缝间流走。
维瑟拉特不会知道酷拉皮卡的忧虑,只有藏在口袋里的手一直在动,一会儿摸摸烟盒,一会儿又敲打火柴盒,别扭地仰着头,目光落在天花板的角落。今晚可能是她第一次冒出这么多小动作。
她也花了点时间思考,寻找着合适的整理话语的方式。
还好,尽管耗费了比预期之中更长的事件,她还是出声了。
“大概是因为,不想看到。”
酷拉皮卡不明白,“什么?”
“不想看到她知道我丢失了记忆之后那种,五官看起来都像要融化了的又惊愕又失望的面孔。”
她低下头,异色的眼眸直直地注视着酷拉皮卡。
“就像之前你露出的表情那样。”
维瑟拉特没有喜欢的东西。她也没有讨厌的东西。
唯独那般失落的表情,会让她感到极其强烈的“不喜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