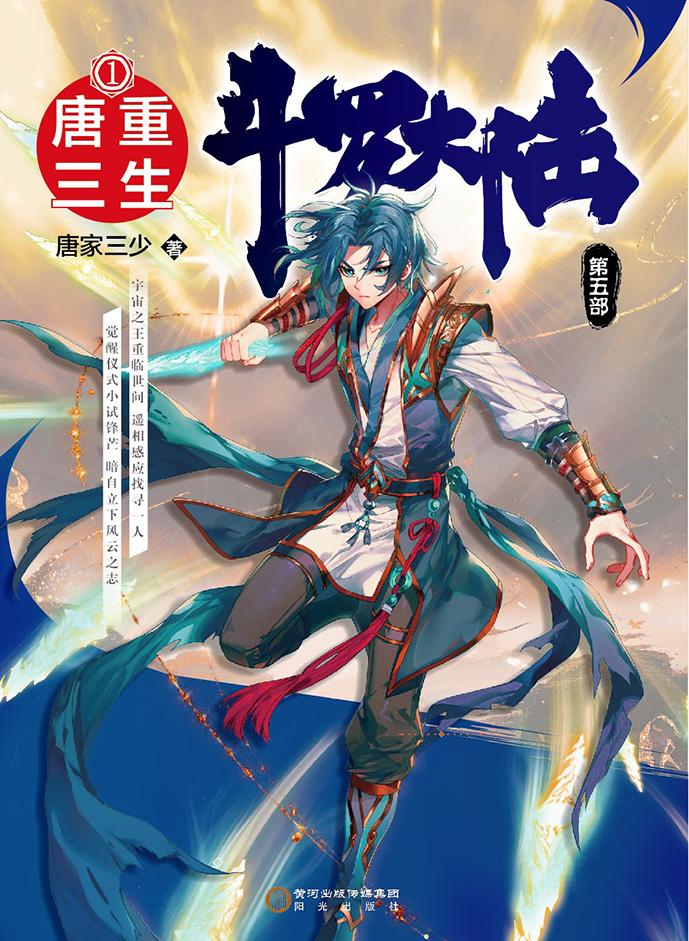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谁要拯救心机美弱受(弯掰直) > 36 落差(第2页)
36 落差(第2页)
她也曾闪过更黑暗的念头。
比如,趁他病重,将他丢在这里,独自去寻找生路。
甚至……让他“自然”死亡。
这样,很多麻烦似乎就一了百了了。
但当她低头,看到凌烁紧闭双眼、眉头紧锁、因高烧而泛起不正常潮红的脆弱侧脸,那些念头就像遇到阳光的冰雪,迅速消融了。
不是因为心软,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——对彻底堕入黑暗、背负一条人命的恐惧,以及对顾宸知晓后可能反应的恐惧。
最终,她还是咬紧牙关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将凌烁一条胳膊架在自己肩上,半拖半抱,深一脚浅一脚地,朝着远处那点隐约的灯火方向挪去。
每一步都沉重无比,凌烁几乎全部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,冰冷的湿衣摩擦着皮肤,带来刺骨的寒意和摩擦的痛楚。
不知走了多久,就在白薇觉得自己也快要撑不住倒下时,他们终于靠近了那点灯火。
那是一个极其简陋、低矮的石头房子,窗户透出昏黄微弱的光。
屋外堆着渔网和破损的木桶,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和柴火烟味。
白薇用尽力气拍打着粗糙的木门。
门开了,一个满脸皱纹、皮肤黝黑、穿着破旧棉袄的老爷爷探出头来,看到他们这副落汤鸡般狼狈不堪的样子,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讶。
白薇急忙想说明情况,寻求帮助。
可她一张口,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得厉害,而且她说的话,老爷爷显然一个字也听不懂。
老爷爷说了几句什么,语调奇怪,发音拗口,是白薇从未听过的方言。
沟通的障碍让白薇瞬间感到了更深的绝望。
她只能拼命地比划,指指昏迷不醒、浑身滚烫的凌烁,又指指自己湿透的衣服,做出寒冷和需要帮助的手势。
焦急和无力感让她眼眶发热。
老爷爷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会儿,又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色和远处黑暗的海面,最终,还是侧身让开了门,示意他们进去。
屋子很小,很简陋。
地上是夯实的泥土地面,墙壁是粗糙的石块垒成,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破旧的木桌、两把凳子和角落里的土炕。
土炕上铺着干草和破旧的被褥。
屋里生着一个小小的炭盆,散发着微弱的热量,却已经是此刻无上的温暖。
老爷爷帮忙将凌烁扶到炕上。
白薇顾不上自己,连忙去摸凌烁的额头,烫得吓人。
她焦急地看向老爷爷,比划着“水”、“药”的动作。
老爷爷似乎明白了,转身去灶台边,用粗陶碗盛了一碗温水过来,又从一个脏兮兮的布包里摸索出几片晒干的、不知名的草药叶子,示意白薇给凌烁喂下。
白薇看着那几片来历不明的干叶子,心里直打鼓。
但她别无选择。
她费力地扶起凌烁,让他靠在自己怀里,一点点将温水喂进他干裂的嘴唇。
凌烁在昏迷中本能地吞咽了几口。
至于草药,白薇犹豫了一下,还是掰下一小点,混在水里让他喝了。
死马当活马医吧。
老爷爷又找来两套虽然破旧但还算干净的粗布衣服,指了指旁边一个用草帘隔开的小小空间,示意白薇去换下湿衣服。
白薇谢过(尽管对方可能听不懂),拿着衣服走到帘子后。
脱下冰冷湿重的衣物时,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,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换上粗糙的、带着皂角味的粗布衣服,虽然不合身,但干燥的感觉让她稍微好受了些。
她摸了摸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,心中稍安。
她走出来,看到老爷爷已经将凌烁的湿衣服也扒了下来,给他换上了另一套男式粗布衣,并盖上了那床散发着霉味和阳光混合气味的破被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