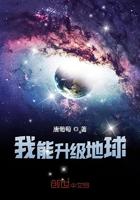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秦凰記 > 瘋狼嘯月(第5页)
瘋狼嘯月(第5页)
铁蹄砸向冻土的闷响如滚雷碾过地心,冻硬的草皮在蹄下爆裂,碎冰与尘土混着凝霜的草屑冲天而起,在荒原上拉出一道灰白色的浪潮。骑兵阵型呈楔形突进,最前排的骑手压低长矛,矛尖寒光连成一线,如巨兽的獠牙。
蒙恬的玄色令旗劈下时,城墙上的秦弩手听到了两种声音——
弓弦震动的嗡鸣,如千万隻毒蜂同时振翅;
鮫筋索在箭尾缠绕时,鳞纹摩擦发出的嘶嘶声,像毒蛇蓄势待发。
“咻——叮铃!”
第一波铜铃箭离弦的刹那,匈奴人看见天空暗了一瞬——
那不是乌云,而是叁千支箭矢同时遮蔽了天光。箭簇破风的尖啸匯成死亡的浪潮,铜铃在风中震颤,声波如无形的刀刃,刺进战马的耳膜。
箭矢坠入马群的瞬间,草原上炸开诡异的交响:
铜铃的尖啸,高频刺耳,如恶鬼狞笑;
鮫筋勒进马腿的闷响,筋肉纤维被绞断的“咯吱”声清晰可闻;
战马惊恐的嘶鸣,不似牲畜,倒像被活剥皮的人发出凄厉哀嚎。
一匹枣红马前蹄跪地时,骑手清晰地听到“咯吱”声——不是骨头断裂,而是筋索内的鮫鳞在收紧时彼此刮擦,像千万把小銼刀在血肉里搅动。
阿提拉的瞳孔里映出这样的画面:
亲卫队长被叁根筋索绞杀
一根缠颈,两根分缚左臂与马鞍。西域良驹发狂般转圈,将主人拖行在雪地里。勒断的胳膊还掛在鞍韉上,手指保持着抽刀的姿势,断骨处筋肉虯结,鲜血在雪地上泼出扇形轨跡。
战马堆成的尸山
被绊倒的战马堆叠成小山,最底层的马匹还在抽搐,压在上面的同族却因筋索交错,把彼此越捆越紧。铜铃在尸堆里微弱震颤,像为死者敲响丧鐘。肠肚从破裂的马腹流出,热气在寒风中凝成白雾。
阿提拉耳畔灌满死亡交响:
风声裹着秦军的战鼓,节奏如心跳;
垂死战马的哀鸣中混着铜铃碎响;
还有……羽箭破空的尖啸直逼面门!
他猛地侧头,箭簇擦过颧骨,带起一串血珠。叁百步外,那支箭深深钉进狼头大纛的旗杆,箭尾的幽蓝鮫筋在风中狂舞,如活物般缠绕而上。
——直到这一刻,他才真正看清城墙上那道素白身影。
沐曦立在雉堞边,素白狐裘被北风掀起。她垂眸俯瞰战场,指尖轻轻摩挲着一卷鮫筋,唇边笑意比冰刺更冷。
太凰伏在她脚边,银白皮毛溅满血点,琥珀色的瞳孔锁定阿提拉,喉间滚出低吼。
阿提拉的心脏狠狠一颤。
「你……」他舔去唇角的血,狞笑,「中原王的女人,竟有缚狼之智?」
他猛地扯住韁绳,战马人立而起,对着城墙长啸:
「凰女!今日之败,我记下了!待我踏破咸阳,必让你成为草原的可敦(皇后)!」
声音裹挟着北风,直刺城头。
沐曦未语,只是轻轻抬手——
「咻!」
一支铜铃箭破空而来,精准钉在阿提拉马前叁尺。箭尾系着一条染血的鮫筋,如警告,如挑衅。
嬴政的身影出现在她身后,玄衣冕服,眸如寒星。他揽住沐曦的腰,居高临下地睥睨败军之将,唇边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
「寡人的女人,你也配覬覦?」
---
残部退回草原后,阿提拉摔碎酒囊,暴怒如雷。
「查!秦人用的什么妖术?!」
斥候战战兢兢捧来一段缴获的鮫人筋索:「单于,是此物……据说出自楚宫秘宝,经凰女亲手改良。」
阿提拉攥紧筋索,索上残留着淡淡的幽香,似雪中梅,似帐中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