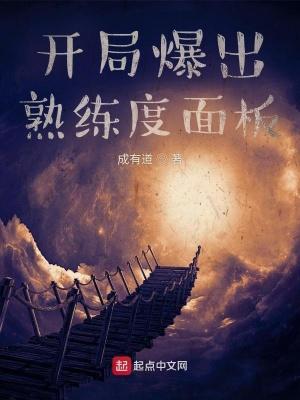舒文小说网>我真没想霍霍娱乐圈 > 575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(第2页)
575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(第2页)
苏小武没否认,也没解释。他只是合上那本《溯源手札》,指尖抚过封面上磨损的烫金字母,像抚过一段被时光摩挲过的旧木。
“尤老师,”他忽然开口,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,“分析结果导出一份PDF,加密,发我邮箱。另外——”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尤海峰因激动而泛红的脸,以及他怀中那台嗡嗡发热的笔记本:
“把那段原始音频波形,单独截出来。不要任何处理,就最原始的WAV。明天一早,送到我办公室。”
尤海峰愣住:“啊?可……可这还不是最终版啊!连歌词都只有一段!”
“够了。”苏小武打断他,声音很轻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,“它需要的不是更多,是第一次被真正听见。”
这句话像投入深潭的石子,在每个人心里漾开一圈无声的涟漪。
尤海峰下意识点头,抱着电脑转身就走,临出门又刹住,回头问:“那……布莱曼女士的演唱版本?”
“留着。”苏小武说,“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回响。我们先听自己的。”
门轻轻合上。
录音棚里只剩下三人。洛兰·布莱曼没再提合作细节,也没追问那“另一个世界”是什么意思。她只是走到窗边,推开一条窄缝——窗外,京都的夜色正浓,远处奥运主体育场的轮廓在霓虹中若隐若现,像一座巨大的、尚未冷却的熔炉。
“你知道吗?”她背对着他们,声音融在夜风里,“我最后一次回斯卡布罗,是十二岁。那年夏天,我站在城堡废墟的断墙上,看着海鸥掠过教堂尖顶。我妈妈在我手里塞了一小束干花——芫荽、鼠尾草、迷迭香,还有百里香。她说,‘记住它们的味道,兰兰,它们会带你回家。’”
她顿了顿,没回头,但肩线微微放松下来。
“后来我飞得越来越远,唱的歌越来越多。可那些味道,渐渐淡了。直到今晚……”
她抬起手,仿佛还能触碰到那束干枯的香草。
“直到今晚,它们突然回来了。不是记忆里的味道,是活生生的,带着咸涩海风和古老石墙气息的味道。”
小青蛙悄悄抹了把眼角,假装在调试耳机。
苏小武没说话。他走到控制台前,调出刚才录制的原始音频文件。波形图在屏幕上平稳延伸,像一道沉默的海岸线。
他点击播放。
没有伴奏,没有修饰,只有洛兰·布莱曼清透、微哑、带着叙事感的嗓音,赤裸裸地流淌出来:
“AreyougoingtoScarboroughFair?
Parsley,sage,rosemary,andthyme……”
这一次,没有钢琴的支撑,没有合成器的烘托。那声音更轻,更薄,却奇异地更重——重得压弯了时间的脊背。
当唱到“Remembermetoonewholivesthere”时,苏小武看见洛兰·布莱曼的肩膀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她依旧背对着他们,但抬起的手,在月光下微微蜷起,像要接住什么,又像在松开什么。
一曲终了。
寂静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沉,更暖。
良久,洛兰·布莱曼转过身。她脸上没有泪痕,但眼睛亮得惊人,像刚被海浪洗过的星辰。
“苏,”她说,“这首歌,不能只给斯卡布罗。”
她走向控制台,指尖悬停在播放键上方,没有按下,却像握住了某种无形的权杖。
“它应该去所有有故乡的人心里,种下一小片海。”
苏小武看着她,终于笑了。那笑容里没有惯常的疏离或调侃,只有一种深切的、近乎疲惫的释然。
“好。”他说,“那就让它,从这里出发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签字笔,在尤海峰匆忙塞给他的那张空白乐谱纸上,写下第一行字——不是歌名,不是署名,而是一行极小的、几乎难以辨认的铅笔备注:
【献给所有把乡愁折成纸船,却忘了它本该漂向大海的人】
笔尖划过纸面,发出沙沙的轻响。
窗外,东方天际线悄然漫开一丝极淡的灰白。奥运倒计时牌在远处楼宇间无声闪烁,数字跳动,指向新的二十四小时。
而在这栋城市心脏位置的玻璃幕墙大厦十七层,一座幽蓝灯火的录音棚里,一首不该属于这个时代、却注定属于所有时代的歌,刚刚完成了它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心跳。